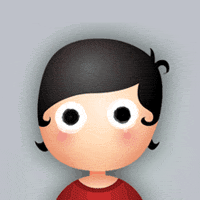一个下午
初夏,坐在结满果实的枇杷树下
我们喝茶,在交谈的间隙惊叹云朵的变幻
你说荷尔德林刚过三十就得了癫狂症
耽于幻想而“孤身独涉”,怎么会知道
沉默这东西,几乎无所不能
总在那些不朽的时刻里,投掷虚空
什么正在降临?
“通灵者”从体内掏出黑夜
我常常感到,语言所携带的奇状眩晕
击中我的额头,眼前影影绰绰
时间皆为陈迹,诗歌像一座巨大的矿床
我需要彻底地俯身含住泥土
从它丰腴的泪水里,获取自身的轻盈
或者,沉溺于词语的水流
让隐藏的漩涡,成为一只精巧的复眼
夏夜河畔
万事皆空,除了你闪烁的嘴唇
——策兰
一条河流,该有怎样的冥想
夏夜的风秩序井然
只要和水在一起,我自身的抽象就
变得越来越具体,如岸边的细沙
无论如何也难获欢欣
年少的孤独,更倾向于那些
喧嚣的假象,将酒杯里无尽的空洞
饮入胃中,而厌倦,仅仅是虚晃而过
一场可能的暴雨湮没地无声无息
黑暗中没有人聊起生命的本质
我们只是谈论生活的奔波
一切的局限,都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由
远处,月亮困于水面,晕开了一束光芒
我的村庄
那个喝下农药的妇女,那个溺亡的孩子
那个上吊数日才被发现的老人,那个
傻瓜,大小便失禁,对着空气破口大骂
在我的村庄里,这都不是新鲜的事情
一九五九年夏天,所有本该葱茏的树
都赤裸着身躯,同样赤裸的,还有我的
正值壮年的祖父,他挖好了一座坟
却再没有力气,将亲人薄薄的棺木
安放进去,他,只淡淡地望了望云彩
骂了句老天爷我日你娘
我不爱这村庄,它埋葬了我太多的祖辈
那里的植物从我祖先的骸骨中生长出来
鲜活,旺盛,像一面旗帜,充满生命力
使我苍白的手指不敢触摸
这片土地在一条瘦弱的河流沿岸
这条河流最终汇入滚滚长江
我,只是溯游而上的人,墓碑早已刻好
此刻,正静静放置在村庄的某个地方
等待我,而我,或许,永不归来
潜行者
——致敬保罗·策兰
一个钓鱼的人在塞纳河下游
发现了一具诗人的遗体,七公里外的
米拉波桥呈现拱形的眩晕
“那里,一个最痛苦的在说,永不”
语言之途太过漫长,以至于
需要一种罕见的勇气与良知
支撑那些艰涩的,简短的,失衡的
未被损毁的“悖论式的修辞手段”
那个投河自尽的诗人
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书桌上
一本打开着的《荷尔德林传》中
他划出这样的句子:
“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内心的苦井里”
前奏
诗的矛盾,在不断地推翻与重构之中
想象的难度,令身体沦陷于虚无
而蹩脚的词语
有我无法改写的瞬间
唯有一个人知道我内心的漩涡
她迷失在夏日,一扇虚掩的门
门后是无尽的田野
象征永不衰老的爱情
无论一生如何度过
我们都应该一起相爱,一起沉默
看晚风吹走所有年轻的寂寞
夕阳在你的额头上徐徐沉下
在我听过的无数谬论里
我只相信你,你说:
钟声滴答,是时间开始的前奏
搅拌机和黄昏
那些混凝土,妨碍了黄昏的秩序
搅拌机轰鸣,我仿佛听到
单薄的风,被撕裂的声音
远处的水杉和云朵,正保持沉默
凋零的鸟鸣,岑寂的喧嚣
我原谅它们一切的回声
黄昏令万物生出褶皱
那些新鲜的预言和爱情,一瞬间就
垂垂老矣
直到黑夜折叠了我们的身体
出窍的灵魂,已经变为化石
它们悲哀的脉络竟如此漫长
像是从未有过一次短暂的欢愉
《信阳文学》
主编:杨扬
执行主编:梁深义
编辑:付炜
投稿邮箱:1400432323@qq.com
编辑微信:fuwei-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