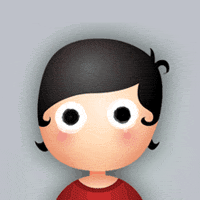本文转发自订阅号“B10现场”,内容是月前明天音乐节期间对首次赋华演出的德国经典前卫摇滚乐队faUSt的采访,感谢阿飞、歪,及明天音乐节的各位。
B10现场
▼
幕后:faUSt在明天音乐节
Behind the Scene: faUSt at Tomorrow Festival
faUSt访谈(节选)
2016.05.16
Werner “Zappi” Diermaier(鼓,乐队老成员)Jean-Hervé Péron(贝斯、人声、吉他,乐队老成员)Maxime Manac’h(键盘、敲击乐、吉他,乐队新成员)李桐慧 Anla Lee
Anla - A; Jean-Hervé Péron - J;
Werner “Zappi” Diermaier - Z; Maxime Manac’h - M
A:演出中你播放了一些不断重复的句子,比如“圆形是美的(rund ist schön)”,还有中文的“这条路是正确的”。这些句子是什么意思呢?J:这么说吧,一方面,它们有哲学上的意义,而另一方面,它们又毫无意义。这是达达主义。所以,如果我说“rund ist schön”,那是因为它的发音——“rund - ist - schön”——它里面包含了不同的声音,而我喜欢这点。至于哲学层面,它的确如此,一切圆的东西都是无害的。你看,这是一个角,如果我的头撞上了它就会很疼,而如果它是圆的那我就不会受伤。圆形是美的。再比方说,怀孕的女人……当她们孕育一个新生命的时候,是圆的。很美。圆是永恒的。它无始无终。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这个句子。其实这个句子是我们让阿飞录的,这样听众们就能听得懂。因为或许你们中的一些人会说英语,但有一部分观众是不懂的。我希望确保他们能尽可能明白我们所表达的东西。关于另一句,“这条路是正确的”,则有更多的达达主义哲学的成分在里面。它也是鼓舞人心的。无论你走哪条路,无论你选择了哪条路,音乐上,亦或是生活上、、工作上,无论你选择了哪条路,你都应该这样想:“这条路是正确的。这是我的路,是正确的路。”所以说,这是一个积极正面的想法。
A:我们觉得你们的现场演出和你们的专辑有很大的差别。从近期的视频里看来,你们使用了一些不常见于舞台的设备,比如煤气罐、水泥搅拌机、石头、热水壶等等。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J:嗯,首先,我得说,艺术家们可能并没有确切地意识到自己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那是来自内在的。它们可能来自你的肚子,或者心脏,但很少是来自头脑的。那不是一种计算。当然,有一些艺术家会那样做,但很显然我们不会。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了它背后存在着一些原因。比如我们在舞台上安排了织毛线的女士们,是有很多原因的。心理层面上说,我们喜欢把观众置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观众不应该觉得“这是正常的”。他们应该想:“发生了什么?这是什么?这不正常。”然后他们就会投入其中。他们处于不平衡的状态,这不是日常生活。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听,必须认真看”。总之,这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心理学的伎俩,但它也拥有相当强的冲击力。这些织毛线的女士们会让你想起一些非常原始的东西,让你想起你的母亲在织毛线的场景,以及你小时候的世界,一切都很安宁,而你感到安全。因为这种织毛线的场景而产生了一种安宁的感觉,就像牛在吃草,那种气味……这种安宁让你感到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观众入场时,他们是非常兴奋的,但他们见不到faUSt,只能见到这些织毛线的女士,安宁。这让他们专注。
你也提到了水泥搅拌机。水泥搅拌机也是充满了符号象征的。非常强悍,极具象征性。它就像是永恒。因为有了水泥搅拌机,你就能建造房屋,建造文明。它们被不断地建立起来,建立起来。然后,嘭!一段时间之后,全部轰然倒塌。文明瓦解。然后它们再一次生长。家庭就是一个巨大的文明,它们无处不在。然后,“嘭!”,它们倒塌了。成吉思汗曾经多么伟大,铁蹄踏遍世界。倒塌了。然后它们又一次卷土重来,又一次土崩瓦解。这就是永恒。就如同水泥搅拌机所做的那样,它不断地转动、转动、转动、转动……建造房屋,倒塌,然后再建。永恒。这就是原因。关于水泥搅拌机我还能说很多,不过现在就到此为止吧。还有,在水泥搅拌机和织毛线的女士们之间也有着强烈的对比——一个是非常坚硬、野蛮、工业的,一个则是非常柔软而日常的。
至于煤气罐,有两个原因。视觉上它给人有点危险的感觉,但主要是为了它的声音。他(指Maxime)是煤气罐专家。他热爱金属的声音,他喜欢那些粗暴的声音。他总是和这些东西作战,工业、声音,还有金属、钢铁、机械……Maxime很喜欢这种。Maxime的另一面是hurdy-gurdy,非常柔软,非常复杂而又优雅。Z:我们现在演出时用的工具和设备比起十几二十年前已经少多了。我们以前用更多的工具来创作音乐,比如蒸汽锤、凿岩锤、发动机汽缸等等,为了它们的声音。比如说发动机汽缸,“throoom-iiiillllll”(模仿它的声音),还会有火花。那声音就像是人在哭。人们听到了就会想:“我是不是也该哭?”它听起来像是一种尖锐的哭声,你只要用工具就能发出这种声音。我想是从三年前开始吧,我们总是用水泥搅拌机,有时候用发动机汽缸,但不再用那些能弄出火来的大型机器了,太危险了。比起十年前,对于这些东西在舞台上的使用的管制更加严格了。J:为了健康与安全。没有火花,没有火,没有气,啥也没有。他们想要faUSt,他们想要这个恶魔,但他们不想要危险。所以我们只能选择一条折衷的路。而我必须说,在这儿,在中国,深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国演出——我们把一切都做了,以告诉大家faUSt回来了。我们知道,你们作为主办方为此承担了很多的风险,因为你们接受了我们所有的要求。水泥搅拌机,“好的!我们去弄来!”;织毛线的女士,“没问题!”;煤气罐,“好!有!”;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好的!好的!我们尽力试试!”……所以,我们要给音乐节,给B10现场一个大大的感谢,谢谢你们如此高效而友善的配合!A:你曾说过,你觉得“表演就是在舞台上的日常生活”,是这样吗?J:没错。是的!啊,你记得我说过这话。确实如此。当你把日常生活放到舞台上,它就变成了表演;当你把表演放在舞台上,它就平平无奇了。而我们喜欢荒诞。我们喜欢达达。J:因为他是我们很好的老朋友。我们是在1994年相遇的,在旧金山,我们参加Table of the Elements[1]的同一个展示会。当时我们正在进行美国巡演。灰野敬二当时还年轻。我们在旧金山表演《It’s a Rainy Day》的时候,他直接跳上了舞台,然后发出“Whoooo!”这样的声音。自那以后,我们就有了某种共鸣,某种联系。他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疯狂的。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想我们也是有点疯狂的。所以我们有共同点,灰野和faUSt之间有一些相同的东西。Jean-Hervé Péron和灰野敬二在明天音乐节的舞台上,摄影 肖蔚鸿A:你们和灰野共同演绎了一首歌,我们知道那首歌的歌词来自你女儿的诗作。我们也问了灰野关于这个的问题,他觉得歌词很有趣。你也提到过你让你的女儿接手了你的Avantgarde Festival[2]。你能和我们聊聊你的女儿吗?J:当然可以。Jeanne-Marie是一个……当她还是个婴儿,甚至当她还在她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她就已经和faUSt在一起了,已经和我们一起巡演了。所以,她了解前卫音乐,了解faUSt,了解那个音乐节。这伴随她的整个人生,是她与生俱来的。甚至早在1994年,她4岁的时候,就和我们一起经历了整个巡演。灰野敬二完全被这个小宝贝迷住了,而她总是“噢,Keiji,Keiji”地一天到晚跟在他屁股后面。在纽约,在一个叫Knitting Factory的场地,Jeanne-Marie病得很严重,她发烧了。灰野敬二把所有人赶出了后台,说:“走!走!走!走!只留下Jeanne-Marie。”Jeanne-Marie和灰野。而他就握着她的手,像这样。一直握着。(握住Zappi的手作示范)所以,总之……是的,Jeanne-Marie理解这种音乐。对她来说,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她生来就是这样。她现在26岁,是一个学有所成的艺术生,目前正在攻读硕士学位。我们已经经营那个Avantgarde Festival有18年了,有点厌倦了。它需要耗费非常、非常多的精力。嗯,你们明白的,明天音乐节也是这样的吧。它需要非常多的精力与金钱。所以我们说:“Jeanne-Marie,你来接手这个音乐节吧,用你的方式来做。”于是她就用现在年轻人的方式来经营它。不在单一地点,也不集中在一段时间,他们现在把这个音乐节放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期举办。变成一个个小的音乐节,到处都有,不同时间。关于那首诗,它叫《Harlekin》。Harlekin就是丑角,笨蛋。她写了这首达达主义的诗歌,然后我知道灰野把它翻译成了日文。我们在B10现场表演这首作品的时候,他用日文唱,我则用法文。我觉得这是一首好诗,它是达达主义的,也是激浪派的。Lyrics : Jeanne-Marie CC Varain
Ring, dig a Ding Ding DongBaaa, dada Ding, dig a Ding Ding DongI am a prophet from outta spaceSome may wonder, some may walkRing, dig a Ding Ding DongBaaa, dada Ding, dig a Ding Ding DongYou are asking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never listenThis may be a game and you will never know itこれはゲームのようなもの、君には決してわからないだろう I teach you the rules in a language you never heard before私は君が今まで聞いたことのない言語で君にルールを教えるRing, dig a Ding Ding DongBaaa, dada Ding, dig a Ding Ding DongDo you really believe in anything else than power of RAAAAAAAAAW?君は RAW: 生、裸、未加工の力(raw power で剥き出しの力)以外の何かを本当に信じているのか?Ring, dig a Ding Ding DongBaaa, dada Ding, dig a Ding Ding DongI have seen this street before I have walked this alley back and forwardA:你们对14日faUSt专场(灰野敬二为嘉宾)和15日的“明天即兴”演出怎么看?Z:关于faUSt的那场,那是我们自己的风格。我们在演出之前列好了歌单,但实际上整个演出并不是完全按照歌单来的。有一些变动。那是一场普通的faUSt的演出。和我们之前在美国巡演所做很接近,但是……Z:是的。演出本身以及音乐是很不一样的。所有演出都是不一样的。至于15日的演出,我想应该是灰野敬二的主意。灰野希望让它像一个乐队表演,他给我们信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演奏——不是要演奏什么,而是什么时候演奏。他用一种爆炸般的方式来演绎这场即兴。我记得有一段他在弹奏很柔和的吉他,然后突然之间“现在!”(非常大声)。他的这种情绪感染了台上的每个音乐人,所以大家都“嘭!”。四处爆炸。他做得挺好的。这是我第一次听从他人的指挥来演奏——“你现在该演奏了。你现在停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这样,做音乐的这50年来。J:我曾经无数次尝试和Zappi说:“如果你在这会儿开始演奏会比较好。”他会说:“不,我想什么时候演奏就什么时候演奏。”“如果你演奏这种可能比较好……”“不!我想演奏什么就演奏什么!”他从来不听。我和他认识了50年了,我真的试了无数次。然而现在灰野来了,说:“开始演奏。”Zappi就……Z:是呀。这个方式奏效了。我其实是能这样做的——偶尔。(众人笑)A:在舞台上,当灰野指向你,你必须立刻响应,尤其是在Jean-Hervé负责的人声部分。我们很好奇,你们怎么能反应得如此迅速呢?J:嗯,我们怎么说也是专业的,而且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做了。另一方面,我个人非常喜欢讲故事。你看,我有5个小孩,所以生活中我讲过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故事,而且我喜欢这样做。或许有一天我该专门为小孩子们写故事或者讲故事。灰野也知道这一点。他自己想担当人声,同时还想要另一个人声,因为人声在音乐中是很重要的。这和文本无关,和内容无关,而是关于你声音的频率。它和其它任何乐器都不一样,而且能打动人心。它能够触动你的这儿(心脏),而不是这儿(脑袋)。J:所以,对我来说,这样做并不难。在我上台之前,我已经想好了主题。我选择了一只大蟾蜍爱上了一只青蛙的主题。接下来,就自然产生了。剩下的就是讲出这个故事,很简单,它就这样流淌出来,流淌出来,流淌出来,流淌出来……J:这不重要。主要是频率、措辞、表达……文本内容不重要。A:是的。你曾说,从一开始到现在,faUSt在德国都没有很多的听众。那么,对于此次在中国这么一个和德国完全不一样的国家的首次演出,你们有过什么预期或想法吗?Z:是啊,我们的音乐在德国确实没有引起很大的兴趣,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说那是因为我们的音乐就来自本土,没有外来的音乐那么有吸引力。不过我不这么认为,很多德国乐队也在本土获得了成功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知道。或许是因为我们最初是在英国制作的专辑吧。或许这是原因。早年我们在英国比在德国有名气得多。关于中国……我不知道在中国什么是可以做的。我不了解这里的法律。在台上制造火焰是被禁止的吗?或者说是被允许的?我不知道。我知道日本,在日本是可以的。在日本我们几乎可以做所有我们想做的事情,没问题。中国就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不知道。不过,让我很惊讶的是,这里非常地自由。我没想到中国是如此自由的。我感到很自由。J:我没有任何预期,因为除了我在欧洲听闻的那些,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当然,我们听说过各种各样关于中国的事情。我听说过你们的音乐节。你们邀请的艺术家是比较前卫、先锋的这种。所以,呃……我曾想过一点点:我们能在这儿做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能说多少呢?然而我发现,当我们真的来到了这里,就像Zappi刚刚说的,一切都挺顺利的。你可以和人们讲话,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你知道。我在这儿没见到一个警察会跑过来抓着我们看证件什么的。我也没有见到任何人跑来说:“别乱讲话,否则抓你们坐牢!”这事儿我感到抱歉,但这些对于中国的看法确实存在。,在这里你不能说话,不能做这做那。而我们——就如Zappi刚才所说——非常惊讶这里有如此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想法。而且这里的人们非常的友善。在德国或者甚至是在法国,如果你走在街上,冲不认识的人笑,人们可能会起疑心。“你想干什么?”而在中国这里,男女老少……我路过的时候喜欢对人微笑,我对很多人微笑了,而这里的人们总是、总是也对我报以微笑。还有,刚到的时候,我的护照、钱和手机什么的都到处乱放,而很快我发现这样做是没什么问题的,我可以把钱扔这儿,手机扔哪儿,夹克扔这儿……总是会有人来提醒我:“嘿,你东西落这儿了。”今天早上——这就是我早上突然离开的原因——我手机。我不知道我把我的手机忘在哪儿了。我请求一位说中文的女士帮我打我的电话,希望有人会接起来。她打过去,那边立马就接了,说:“是的,我找到了你的手机。我怎么拿给你?”我们就说:“我们住在这边的酒店。”“好的,我两分钟到。”我意思是,你可以试试在德国这样做。或许你能找回你的手机,也或许不能。如果你扔一堆钱或者别的什么在桌上……A:在关于你们乐队的描述中,我们常常能看见“krautrock(泡菜摇滚)”这个词。尽管我们在你们过去的一些采访中看到,你们并不喜欢这个定义,但作为宣传者,我们还是会用到它。大家都在用,人们说你们是这类音乐中做的最好的。你们怎么看?Z: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krautrock”。对我来说,我很难区分哪个是“krautrock”,哪个不是。很多人说70年代在德国创造和演奏的音乐就是krautrock,但我不这么认为。比方说,人们说Kraftwerk是krautrock,但他们的风格和我们很不一样。那为什么他们是krautrock,我们也是krautrock呢?我不知道。我不需要这个词,“krautrock”。J:是的,这个词其实是有点无礼的。“kraut”这个词是二战期间英国人对德国人的蔑称,你知道,因为他们觉得德国人吃很多很多酸泡菜,但事实并非如此,只有德国南部才是那样的。总而言之,它带着点冒犯的意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它。就像如果我们把中国的音乐称为“slit-eye music(眯眯眼音乐)”一样,是很失礼的。所以,我们试着用幽默的方式来接受它,我们甚至还作了一首歌,就叫《Krautrock》。你叫我们krautrock,好呗,那我们就来“krautrock”你!“krautrock”对我们来说大概就是这样。我更愿意我们的音乐被称为实验音乐。不过“krautrock”,其实……当然,宣传者用“krautrock”这个词是没问题的,因为在媒体上人人都知道这个词。所以说,用“krautrock”是无伤大雅的。这不是最好的主意,但没关系。完全没问题。Z:关于什么是“krautrock”,我曾问过一个英国人,他认为是那种有一个不断循环的旋律,并且在这个循环中加入很多噪音、不同的噪音的音乐。或许这就是krautrock吧。
这首歌选自Tony Conrad和faUSt在1972年的一次现场唱片《Outside the Dream Syndicate (With Faust)》
J:你知道Tony Conrad吗?他过世了,愿他安息。他是创造了“minimalism(极简主义)”这个音乐流派最早的那批音乐家之一。但这东西本身并不是他发现的。没有任何人发现了任何东西,它早已存在了数百万年。极简主义无处不在,蒙古人、因纽特人,还有他们之间的……因为他们没有很多的乐器,却有很多的时间。他们必须玩儿点什么,免得死于无聊,而他们又没有足够的乐器,因此他们创造的音乐就非常简单,极简。不过Tony Conrad、The Velvet Underground、John Cale等等的各路人物把它发扬光大了。所以说,在krautrock里面我们也有一些minimalism——这就是刚才Zappi所说的,比如一些非常简单的节奏,“do-boom-do-doom, ku-chi-ka-doom-doom, ku-chi-ka-doom-doom…”,又或者是一个单音,“boom, boom, boom, boom…”。总之,这已经足够触发你内心的某些情绪了,剩下的就都在你的脑子里进行——是你在创作这个音乐,我们只是扣动了。有一些音乐人会在这种循环里面加入任何他们想要加的东西,因为里面空间很大,你可以放很多东西进去。(作为听众的)你自己的东西,还有音乐人的。
J:我是。
Z:在60年代,我觉得我是个嬉皮士,但到了70年代中期,我觉得我不是。嬉皮士其实并不真实。
J:你说什么?
Z:60年代的嬉皮士都在撒谎。
J:去你的,老兄!
Z:很多嬉皮士说:“我如此自由!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但他们的内心却并非如此。
J:好吧,我原谅他。我是个嬉皮士,而嬉皮士是宽容的。他在胡说八道。他不了解嬉皮士。
M:我不是嬉皮士,绝对不是。
J:所以我是这里的唯一一个。
M:当然,我是喜欢嬉皮士的。不过Jean-Hervé,你也不是嬉皮士啊。
J:可我有一件嬉皮的夹克。我有一只狗。我喜欢赤脚走路。
M:但你比很多的嬉皮士要积极向上,而且比他们更有智慧。
J:好吧,好吧。
Z:你没有自由的。
J:但我很乐意有啊。
Z:你只能是很乐意“有过”。
J:好吧,你看看,所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总之,大多数时候,当有人问我们问题,我说是,他就说不是,我说你好,他就说再见。而我们已经这样相处了50年啦。
A:或许这就是你们能够长久相处的秘诀呢。
J:或许吧。
A:有人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摇滚乐在70年代已死。而如今,网络和科技正在杀死音乐人的想象力,杀死他们的才华。现在所有的音乐都是娱乐。你们对此怎么看?
J:呃,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里面,的确有一些是真的。这很有趣,是的。现在制作和分享音乐的方式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就像生活中的万事万物一样,有阴有阳。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有冷,有暖,诸如此类。
数码世界存在这样的一个风险,那就是人人都能创作音乐,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音乐就会是有意思的。但是任何人都能够去做了。你只要上Bandcamp或者随便什么东西,随便敲几下,“嘭”,一首歌就出来了!在现在这一切都是可行的。然而那是好的音乐吗?我不确定。另一方面,那些真正投入到音乐的艺术家们,那些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艺术家们……艺术家对于他们的观众是要负责的。你在传递信息。这就像和小孩子们说话,如果你对他们说了错误的事情,他们也会相信你的。所以,你得确保你不要把垃圾输送给人们。
数码的制作方式扩展了可能性。你可以创造新的声音。有更多的乐器任你发挥,而且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就可以达成——在你的电脑上。你可以演奏笛子,你可以有一整个弦乐团。你可以拥有雪花飘落在喜马拉雅山顶上的声音,只要你想。这些都可以实现,你能够拥有这一切。这是好事。它并没有杀死你的想象力——如果你是一位艺术家,如果你是一位真正投入的艺术家。
网络,呃,是的,它对艺术家产生了威胁,因为任何人都能免费下载我们的音乐。不过这也挺好的。这就是它存在的方式。由此他们得以听到我们的音乐了,又或许某一天他们会想要实体了。他们会想要指尖真实的触感,目睹真实的画面,你知道,看到那些真实的CD、黑胶唱片。你可能已经发现了,黑胶正在经历一场复兴。在欧洲,我们卖出的黑胶比CD要多得多。像10年前,我们只能卖出CD,没人要黑胶:“不,那太老土了,我们才不要呢。”而现在完全相反。在中国也是这样吗?是的?所以说,这是一种新现象。
另一方面,它的好处在于,我们这些艺术家,比如他来自法国,他来自奥地利,我住在德国……但我们能够交流。我们能够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互相发送曲目音频。
Z:不过用数码的方式演奏是完全另外一种感觉。比如说,你可以录下摔碎一个玻璃杯的声音。你可以把它录在你的键盘里,然后按几个键,声音就出来了。但是在舞台现场表演要好玩得多。拿一个真的玻璃杯,拿一个麦克风,真的把它摔碎在地上。现场表演会更有意思。
J:是的。总体来说,现实的东西会比虚拟的更能打动人。你看看Facebook就知道了。我有……我不知道,6000个好友吧。我才没有6000个好友呢。现实生活中有两个好友我就很满足啦。我的狗,我的妻子,我的孩子,Zappi,Max,阿飞……
Z:我的车。
J:“我的车和我的茶……”(哼唱)总之,你懂我意思就好了。现实和虚拟。我相信我们正一步步朝着虚拟的方向迈进。走在大街上,人人手上都拿着个手机。人们虽然走在一起,但我拿着手机,他也拿着手机。明明是在现实之中,却活在虚拟里。我想这就是未来。这很糟糕,它不会通向任何地方。
A:我们知道Maxime喜欢演奏一些奇奇怪怪的乐器。你能稍微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M:首先,我在舞台上会演奏一些电子设备,还有吉他。有时候我也演奏hurdy-gurdy,有时还会加上一些效果。Hurdy-gurdy是一种诞生在1300年前的法国中部的古老乐器,不过你也能在东欧找到一些不同的版本。它可以说是一种带有转轴的小提琴。通过不同的琴弦,它能够发出一些连续单调的低鸣,但你也能用它创作出旋律。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乐器,因为它听起来很传统,而当你把麦克风放在它里面的时候,它可以发出一些像是在模仿哭声、尖叫声的声音。有时候它听起来像小提琴,有时候又像噪音。Hurdy-gurdy是一种非常特别也非常典型的乐器,我很高兴能把它带入到faUSt的音乐里。
J:这对faUSt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一个崭新的频谱。
M:我受到了一点来自Tony Conrad的小提琴的影响。他在演奏小提琴时保持一个曲调,但持续整整一个小时。有了Hurdy-gurdy,我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我在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调子里混进不同的低鸣,不同的音调和曲调……这是一种有着很多可能性的乐器。
A:你是faUSt的新成员。
M:是的。我来自法国,是一名视觉艺术家。我也是一名画家,也制作一些声音装置。我同时是一名音乐人。我年轻的时候听了很多摇滚乐,krautrock、faUSt、Tony Conrad,以及日本和美国的音乐。我是在2007年认识了Jean-Hervé和Zappi。在那之后,2010年,他们提议我与他们一起在活动和演唱会上演奏。
J:Maxime在我们的Avantgarde Festival上演出过,我们实际上是在那认识的。后来我发现他有来协助音乐节的准备工作,就像志愿者。他最开始就是我们的Avantgarde Festival的“黑奴”。后来他说他也玩音乐,并用一些玩具和噪音玩了一段,我才发现:“嘿,这家伙是个艺术家!”他也做一些视觉艺术,还有……总之,我们的友谊不断加深,然后我们就邀请他和我们一起演奏了,这很好,因为他会演奏hurdy-gurdy,又会视觉艺术,他也很强壮……
M:我是一个很好的劳动力,而他们嗅出了这一点。
Z:而我就喜欢他俩凑在一起说法文,而我一句也听不懂。
J:这是最好的交流。
Z:是的。
faUSt《Listen To The Fish》明天音乐节 2016-05-14
[1] Table of the Elements:一个由音乐制作人兼平面设计师Jeff Hunt创立于1993年的美国厂牌。[2] Avantgarde Festival:Avantgarde Festival是由Jean-Hervé及其家人创立并策划的前卫音乐节,举办地为德国的席福尔斯特(Schiphorst)。现任策划人为其女Jeanne-Marie。*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如有意转载,请联系midori@b10live.cn。
特别鸣谢
第三届明天音乐节特邀影像摄制团队
一个猪蹄